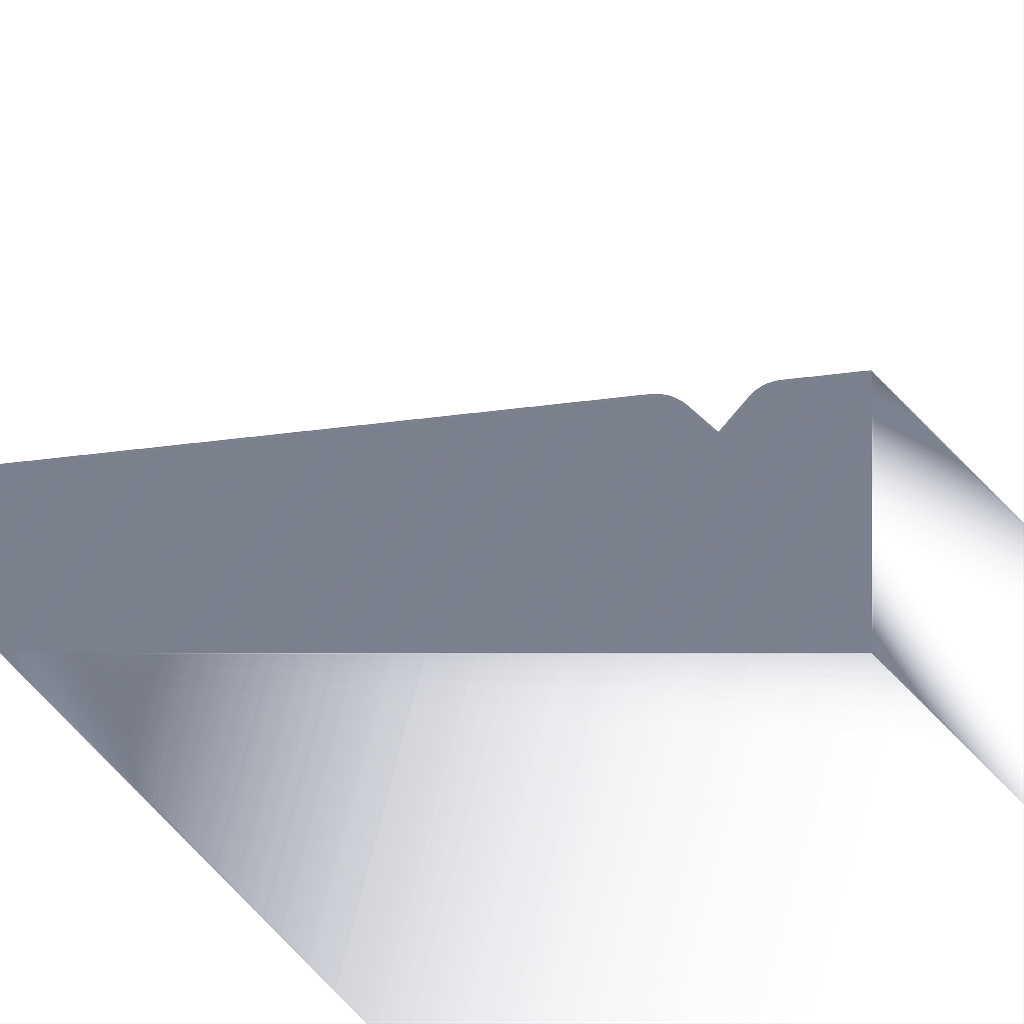《牛津通识读本:尼采》笔记摘抄
《牛津通识读本:尼采》
《牛津通识读本:尼采(中文版)》迈克尔·坦纳
◆ 序言
作者认为,尼采一生的根本关注是痛苦与文化的关系,其立足点不是回避或消除痛苦,而是为了肯定人生而肯定人生必有的痛苦,据此对文化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分级,并寻求一种真正能够肯定痛苦的有内在力量的文化。
尼采主要关注的是人生的根本性痛苦,即生命意义之缺失,这既是折磨他自己的最大个人问题,也是他后来定义为虚无主义的最大时代问题,而他寻求的则是一种能够为生命创造意义的文化,或者退而求其次,一种勇于担当生命之无意义的文化。
在从《曙光》到较晚期的《论道德的谱系》一系列著作中,尼采致力于分析历来道德对抗痛苦的各种方式。其中,有两种基本方式最值得注意。一是同情,即企图通过剥夺个人在痛苦面前的尊严来消除痛苦。二是禁欲主义,即企图通过扼杀生命的本能来消除痛苦。
尼采关心的是伟大而不是善,二者的区别在于,伟大包含着对痛苦的肯定和有效利用,善则一味企图消除痛苦
《快乐的科学》(作者视为“尼采最令人振奋的一本书”)中,他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伟大,便是“赋予个性一种风格”,艺术地规划自己天性中的长处和弱点,甚至使弱点也悦人眼目。另一种表达是,“要成为生活的诗人——尤其是成为最琐细、最日常的生活的诗人”。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就是要做一个能够自我支配的强者,包括支配人性的弱点和人生的痛苦,以此来使生活变得美好。
尼采仿佛如此问:即使生命毫无意义,你愿意它无限次地重复吗?
◆ 道德及其不满
与人如何看待痛苦这一关怀密切相关的,是尼采对伟大而非善的关注。因为,任何伟大都同时伴随着抵御、吸收以及最有效地利用极度痛感的意愿与能力。可以这么说,伟大包含着对痛感的运用,而善则尝试对痛感进行消除。
——“否定道德”意味着:否认人们所谓的道德动机真正激发了人们的行动,断定道德只是一些说法,属于或者粗鄙或者巧妙的欺骗(特别是自我欺骗),是人类,也许尤其是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拿手好戏。“否定道德”可以指:否认道德判断基于真理之上。我们在此承认,道德的确是行动的动机,然而却是这样一种动机:它作为一切道德判断的基础,以将人们推向道德行动。
能否从中确切地得出结论,究竟是应该着眼于人类可能的最长时间的生存,还是应该着眼于人类最有可能的非动物化?
这里的最大幸福指的是人类个体可以达到的幸福的最高程度呢,还是指所有人最终可以平均获得的——必然是无法计算的——幸福呢?而且,为什么实现这种目的的途径只能是道德?(《曙光》,106)
尼采以简明的方式指出:“‘功利主义’。——如今,我们的道德感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对于一些人来说,道德的功利性证明了道德;对于另一些人来说,道德的功利性却驳斥了道德。”
基督教假定,人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对他来说何谓善何谓恶:他信仰上帝,因为唯有上帝知道。基督教教义是一种命令,其根源是超验的;它超越一切批评及批评的权利之上;只有当上帝是真理时,它才拥有真理——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共存亡。
无法从上帝那里寻求伟大之处的人,在其他地方也将无从觅得。他只能否定伟大或者创造伟大。”如若我们承担创造伟大的重担,那么我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都会在这一重担之下坍塌。
◆ 唯一不可或缺之事
——赋予个性一种“风格”,实在是伟大而罕见的艺术!一些人纵览自己天性中所有的长处和弱点,并作艺术性的规划,直至一切都显得艺术而理性,甚至连弱点都悦人眼目——人们就是这样实践这艺术的。这儿增加了许多第二天性,那儿去除了某种原有天性——两方面都需要长期演练,每天付出辛劳。这儿藏匿着无法被去除的丑陋,那儿这丑陋得到重新诠释,成为崇高。不愿变为有形的诸多暧昧被储存下来以备远望之用,其目的在于对远不可测之物进行召唤。最后,当这工作完成时,事物无论大小,如何受一种品位的支配和构建则变得显而易见。这品位是好是坏,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重要,只要是一种品位,这就够了!(《快乐的科学》,290)
尼采提出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审慎地考察自己的天性,并对它进行评定,尽管此时我们还不知道评价标准——什么可以被看做长处,什么可以被看做弱点——并赋予这种天性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就是一般所说的“风格”。对人类性格中的各个要素进行一种“艺术性的规划”确实会给人一种印象:除了注定不受约束的遁世者之外,我们比任何人都更少地受制于外在偶然性。
正是在风格与伟大艺术家的强大个性的张力中,我们发现了至高的成就。
尼采说“这品味是好是坏,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重要,只要是一种品位,这就够了!”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此处使用的标准不仅是审美的标准,而且具有形式特征。相对于它们的结构形式,各个要素的本质只处于次级地位。这使我们再次怀疑,要素事实上是什么是否真的重要。
他写道:“只有一件事是不可或缺的:人必须达成自我满足,不管是通过诗歌还是艺术的方式;只有这样,人才值得一看。”
我们认为一个人具有风格,是因为他具有应付自如的能力,可以将各种分歧以及那些令大多数人感到尴尬或耻辱的经历合并在一起,纳入一个更庞大的系统之中。
我们都应向艺术家学习,同时在其他方面还要比他们更聪明才是,他们纤巧的能力一般会终止于艺术结束而生活开始之处;而我们要成为生活的诗人——尤其是成为最琐细、最日常的生活的诗人。
因为,如果某人的性格中显现出了努力的迹象——如果一个人用意志力使自己看似迷人、温和、沉着、随意,那么,这就是最典型的风格上的失败。
尼采的主张,即赋予人格以风格乃“唯一不可或缺之事”
他所攻击的同情是指投入全部精力来整顿他人的生活,并且,就像我们通常被教授的那样,以高尚的理由而忽略他人自己的利益。因此,将尼采的意思误解成是在宣扬忽视他人的基本要求是很粗浅的(事实上也是非常普遍的)
许多人会认为,坚信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这种道德是他们无法遵循的道德,其原因很明显:他们没有自己的“方式”——他们有的只是各种竞争、需要、焦虑和难题,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他们的个体化目标。
◆ 预言
人若只是当学生,那么就是对老师的最糟糕的报答。
尼采最关心的主题乃是伟大,而舒适、合意、感官满足都不利于伟大之形成。
起初精神是作为一匹骆驼出现的,也就是说,现代人在各种价值的压迫下不堪重负,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传统,由义务和违背此类义务所导致的负罪感所构成,而人不可避免地会违背此类义务。奔向沙漠之后,这匹骆驼先是步履蹒跚,但最终起而反抗。为了战胜一条龙,它蜕变成了一只狮子。这条龙的名字叫做“你应当”,是它给骆驼制造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它宣称:“一切价值都早已被创造出,我就是那被创造出的一切价值。”狮子为了用“我要”取代“你应当”而进行反抗。然而,尽管狮子能够反抗,他也只能为新价值创造自由,而不能创造价值本身。狮子说了一句神圣的“否”,这就是他的结局——他已经为能达到的唯一目的履行了义务。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了。最后一次变化令人吃惊:他变成了一个孩子。
捕食的狮子,为什么必须变为孩子呢?孩子是天真,是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场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个肇始的运动,一个神圣的肯定(“是”)。为了“创造”这一游戏,我的弟兄们,需要一个肯定:这时,精神想要拥有它自己的意志,丧失世界者会获得他自己的世界。
尼采对生活采取了被当今的视频图书馆称为“高度成人化的”一般态度,然而令他着迷的仍是孩子的想法,这个孩子全神贯注于玩耍,时而严肃,时而出神,总是那么天真而无知。
如果每一个周期都按它必须存在的状态,与前一个以及后来的周期严格相同,那么,我们就会对上一轮所发生的事,尤其是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无从知晓。到头来,我们既无法采取措施避免灾难性的结果,也无法带着恐惧或喜悦思索前方的道路。
人们之所以深受永恒轮回这个想法的吸引,原因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一种位于任何单一周期之外的视角,因此,他们可以想见这个周期无休止地重复。甚至很可能就是因为看到自己从被困于周期之中转移到周期之外,以神的视角观察整个过程,才使人产生了那种震颤和无法忍受的重力之感;对于坚定地说“是”的人,则激发出对回归的痴迷。
◆ 占据制高点
我们更要质询这个意志的价值。假设我们欲求的是真理:为什么不是宁求非真理?非确定性?甚至无知?
尼采此时细致审查的不是我们的求真意志,而是我们认为某些主张为真实的意愿,那些将我们轻视的事物和珍视的事物对立起来的意愿。尼采所做的是举出一些例证,来说明我们认定的真理的基本价值事实上来自于其他更为本能的价值。
因为日神以一种可忍受的方式表现生命,它排除一切阴霾之面;而酒神不忽略任何事物,强迫我们去直面那些生存的基本恐惧。
◆ 主人与奴隶
禁欲主义者之所以将某一种痛苦加于自身,不过是为了逃避更多其他类型的痛苦。
朋友们,你们是在告诉我,别去争论什么趣味和品位?可生命的一切就是围绕着趣味和品位的争论!趣味,同时是砝码、秤盘和验秤者;一切有生命者,想要不围绕着砝码、秤盘和验秤者的争论而生存下去,那就注定要遭难!(《查拉》,2,“论崇高的人们”
哲学家说‘善与美一致’,这是不光彩的;如果他还要加上‘与真也一致’,我们应该对他饱以老拳。真理是丑陋的。我们拥有艺术,以免我们因真理而毁灭。
而禁欲主义之所以有强烈吸引力,是因为担心自己受之有愧而恐惧生活中的各种享受。
那些听从教士的命令而奉行禁欲主义的人,并非为了达成任何以禁欲为先决条件的善,而是因为教士强加的负罪感驱使着他们不断接受理应承担的痛苦:通过施加更多痛苦向人们解释人生为何会有痛苦,这其中包含着可憎的残忍,即人要为自己的痛苦负责。
人,这最勇敢、最惯于忍受痛苦的动物,他并拒绝痛苦本身:他痛苦,甚至寻求痛苦,只要有谁给他指示出一种意义,指示出痛苦的。是痛苦的无意义,而痛苦本身构成了长期压制人类的灾难,而!直到现在,这还是人类唯一的意义,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毫无意义……
◆ 后记:尼采与生命保险
从定义上说,卓拔超群是一种稀有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不拥有或不渴望它的人,应该受到鄙视或被清除。
如果一个人用一种新的生活替代充满同情的生活,并且全心体验它,那么,他就会达成这种“新的人道”。
查拉图斯特拉的论断,即“生命的一切都是围绕着趣味与品位的争论”